
13歲時入學全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,當時在協律社的演出中聽到了名唱李花中仙的《推月滿庭》,決定走上聲音的道路。
15歲時進入當代大名唱宋萬甲的門下,學習《心靈歌》和《興報歌》,正式開始了判詞的學習。之後向鄭正烈學習《春香歌》和《水宮歌》,向朴東實學習《心靈歌》《興報歌》《水宮歌》,廣泛涉獵東邊制和西邊制。
光復後,繼續向鄭應民、鄭權鎮、朴綠珠、金如蘭、朴鳳述等當代名唱學習,終身不懈地修煉。
1973年被指定為重要無形文化財第5號判詞藝術保有者,以其深沉的共鳴和克制的唱法被評價為韓國判詞的精神支柱。
她的舞台不僅僅是藝術表演,而是與時代和社區共同分享的共鳴之地。
Q1. 名唱對您來說,判詞是什麼意義呢?
判詞是我生命的全部。就像呼吸一樣,我是為了活著而唱。
許多人稱判詞為「藝術」。但對我來說,它是人們的喜怒哀樂匯聚的容器。
有時候是笑著唱的聲音,有時候是哭著唱的聲音。在舞台上唱歌,不是我的故事,而是代替坐在我面前的人的心聲。
當我發出聲音時,總能聽到父母的嘆息、婦女的辛勞、孩子的笑聲交織在我的聲音後面。聲音就是人們的生活,而我想要一起唱出那份生活。
Q2. 在您演唱判詞的過程中,最難忘的瞬間是什麼時候呢?
戰爭結束後不久,我在一個簡陋的劇場演出的記憶依然鮮明。觀眾們飢餓而疲憊,臉上失去了笑容。
當我開始唱《心靈歌》時,起初大家都是面無表情的。然而,當唱到「心靈睜開眼睛的那一刻」,觀眾席上各處都傳來了啜泣聲。那哭泣並不僅僅是悲傷。
失去家庭的人、失去生活支柱的人們一起哭泣,彼此緊緊相擁。那一段聲音打開了心靈,流下了眼淚,成為陌生人之間心靈的連結。
那時我明白了,判詞不是個人的技藝,而是歌唱著大家共同承擔的時代的眼淚與笑聲。
Q3. 聽說您對弟子們有一句常說的話。
我總是這樣說。
「聲音不是技巧,而是心。」
當然,音準、節拍、發聲和呼吸是重要的。但僅僅這些並不能成為活生生的聲音。如果唱者的心不動,聽者的心也不會動。
我在師父那裡學習時,最困難的訓練不是修飾聲音,而是學會清空和充實我的心。經歷過深刻生活的人所發出的聲音,即使不加修飾也會有共鳴。因此,我叮囑我的弟子們要成為能夠將生活轉化為聲音的人。
Q4. 為什麼判詞的傳承和保存如此重要呢?
傳統並不僅僅是抓住舊的東西。在其中包含了祖先的嘆息和喜悅,社區彼此支撐著生活的故事。
忘記判詞,就是忘記我們民族是如何笑和哭的。如果那段記憶消失了,我們將來該依靠什麼生活呢?
我相信,保護判詞不僅僅是保存音樂,而是延續人性和社區的記憶。
Q5. 對於今天生活的人們,判詞能帶來什麼樣的共鳴呢?
今天的年輕人過著快速而激烈的生活。然而,空虛和孤獨並不容易消失。
聽到判詞時,會在古老的聲音中發現自己的心。笑著哭泣,在悲傷中再次尋找希望。這就是判詞的力量。
判詞這樣低語著。
「生活是一個充滿喜悅與悲傷的故事。」
在一起聆聽和分享那個故事的瞬間,我們獲得了安慰,重新獲得了生活的力量。
Q6. 最後,您有什麼想留給後代的話嗎?
我一生都在唱判詞,但那不是我的歌,而是我們的歌。聲音會消失,但共鳴將留在每個人的心中,跨越世代延續下去。
我相信。
如果有人真心地延續聲音,判詞將超越千年,讓另一代人哭泣和歡笑。直到那一天來臨,聲音將以我們的呼吸活著。
📌 編輯者註
這篇文章並非真實對話,而是基於金素姬名唱的生平、活動以及留下的記錄和證言重構的虛擬訪談。
《Breath Journal》希望將傳統傳遞為不僅僅是過去,而是與今天的生活相連的活生生的共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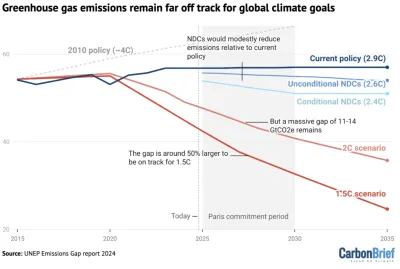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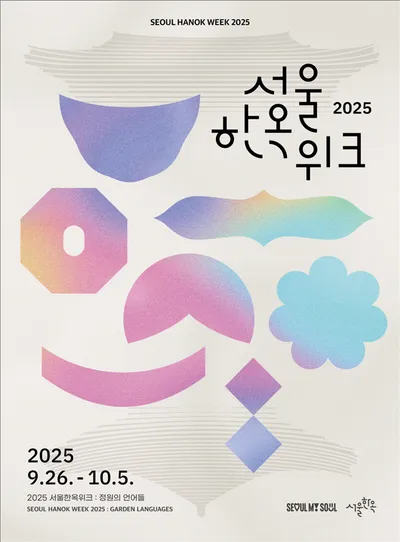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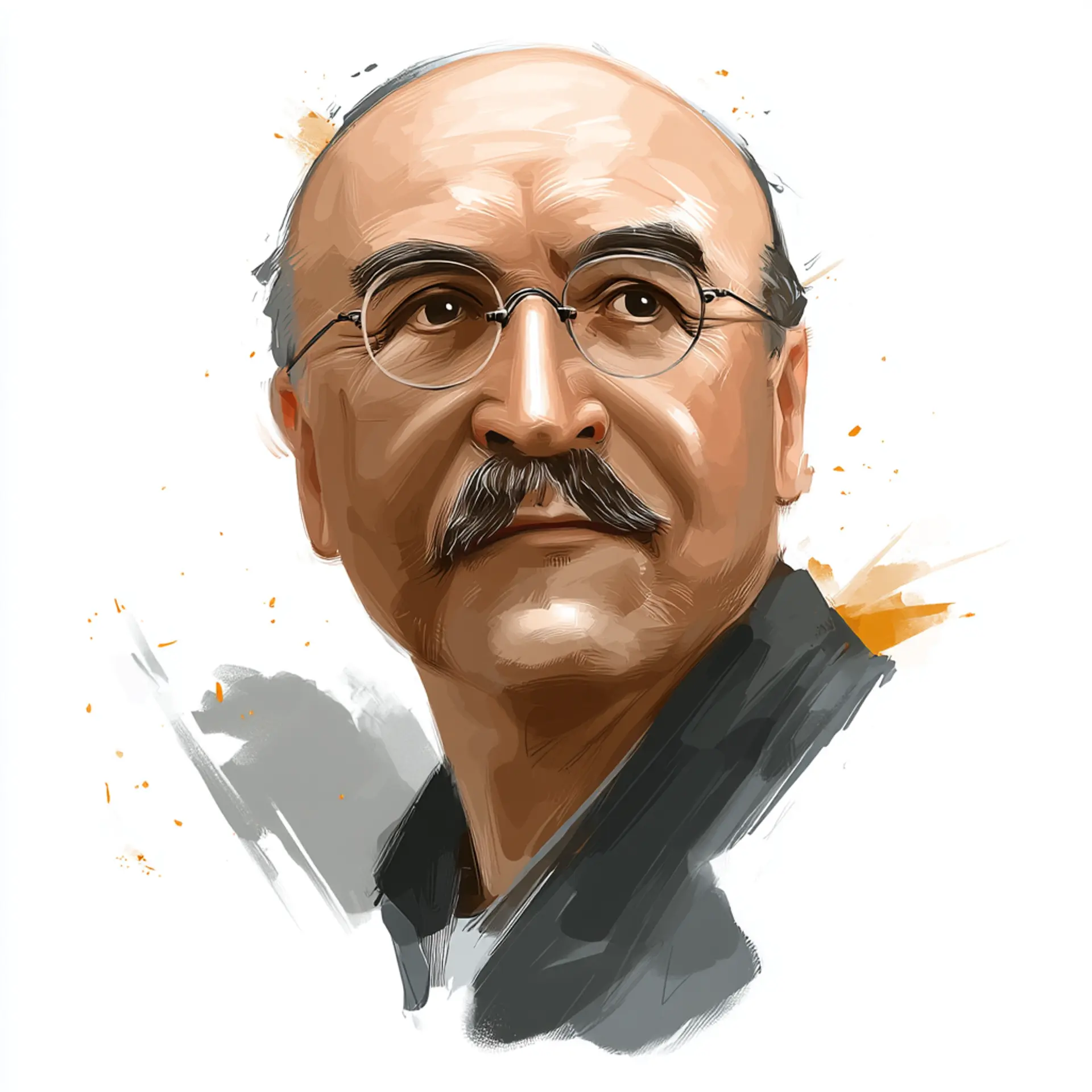

댓글 (0)
댓글 작성